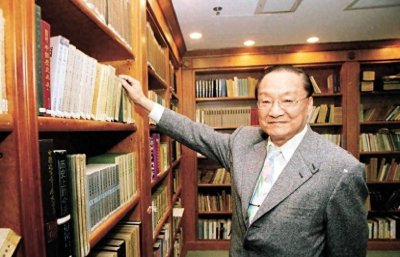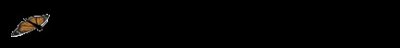陈源:被鲁迅“暴打”的正人君子,65年被法国军警强行抬出使馆
陈源:被鲁迅“暴打”的正人君子,65年被法国军警强行抬出使馆
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现代评论派的主要成员。陈源是鲁迅的主要论敌之一,鲁迅回战陈源的文章多达篇。陈源骂鲁迅的文章大多是通过杂志《现代评论》发表的,后来人们说鲁迅骂现代评论派,其实主要也是骂陈源。
《现代评论》的主要撰稿人有胡适、陈源、徐志摩、王世杰、唐有壬等,胡适是这个刊物的首领。
现代评论派在建国后,多被认为是反动反人民的,其实产生这种认识的主要原因是现代评论派在政治立场、文艺观点上都比较复杂—现代评论社是由太平洋社和创造社合并组成的。
成员里既有无产阶级革命的拥护者,如李四光、丁西林、陈瀚笙;也有共产党人和进步倾向的文人,如陈启修、田汉、胡也频等;也有一些当时偏右的人,如胡适、陈源,甚至是后来成为敌人的王世杰、唐有壬等。
因为政治思想倾向比较开明,在发表文章时没有宗派之见,使现代评论派充满了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思想成分也就十分复杂。他既宣传过马克思主义,也反对过共产党。由此可以说,很难能单独拿出一个人来代表现代评论派,因为它的成分就是多样复杂的。故而,鲁迅骂陈源,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骂现代评论派的其他人。

一、女师大风潮论战
陈源和鲁迅对战的开始是因为在女师大风潮里有不同的立场。鲁迅是在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大闹国耻纪念日,开除六名学生后表明站在学生这一边,忍无可忍地指责拥护校方这类人是“凶兽和羊”:当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相;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就现凶兽样。而陈源从一开始就卷入风潮,虽然自己给自己披着“公允”的外衣,但言及心声都是站在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和女师大校长杨荫榆一边的。
早在1925年2月7日,陈源就在《现代评论派》第九期上发表文章指责学生运动;3月21日,更是发文重申自己的观点,斥责学生,并暗暗地挑拨是非,他说:
“女师大中攻击杨氏的学生,不过是极少数的学生;而这回风潮的产生和发展,校内外尚别有人在主使。”
“校内外尚别有人”指的是谁呢?女师大风潮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文化界和京沪学生界的支持和声援,而既站在学生这边,又能成为“校内外”人,即在校内任职又在校外同文化界等有显著关系的,指的不就是鲁迅吗?
既然一方先行发难,那么鲁迅自然也不退缩,开始反击。
5月27日,鲁迅和其他六位教授联合发表了七教授《对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表明校方发表的一系列声明是“诬妄”,坚定地站在学生这一边。
5月30日,陈源在《现代评论》第二十五期发表《粉刷茅厕》一文。他在文章的一开始就说:
以前学校闹风潮,学生几乎没有对的;现在学生闹风潮,学生几乎没有错的对我这种人来说这两种观念都是迷信—如此一番来显示他的“公允”。
在“公允”完了之后,又说这次的女师大风潮,其实是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优势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还说他本来是不信“平素所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但是这篇宣言一出,就免不了让人有这种想法了;陈源还说,这种闹事已好像一个“臭茅厕”,“人人都有扫除的义务”,要教育局彻查,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就是希望政府方面要加大镇压力度的意思。

陈源已经把女师大比作“臭茅厕”了,他的倾向性其实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了,如果干脆地表明自己站在章、杨一边,也还算君子,却要摆出一副假绅士的嘴脸,打着公正的旗帜偏袒其中一方。
鲁迅觉得陈源虚伪可笑,在给许广平的信里面,就写到他“装作局外人的样子,真会玩把戏”。鲁迅又接着说,陈源说什么“某籍某系教员所鼓动”,倒不如直说是“国文系浙籍教员”,这个话里话外不就是指是自己是罪魁祸首吗?
不过,陈源既然提出了籍和系的问题,鲁迅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由于陈源和杨荫榆都是江苏无锡人,所以鲁迅就挖苦道,流言这种鬼蜮的手段本来就不该相信,但有人使用这种武器,要用籍贯说事,那么只要查查他自己的籍贯,一看是在为同籍的人说话,就算他自己装作公允的样子,也容易让人怀疑,还说这种以己度人心态就好像:
“偷汉的女人的丈夫,总愿意说世人全是忘八,和他相同,他心里才觉舒畅。”
言语之辛辣,可谓入木三分。
鲁迅用的这招果然叫热爱造谣者自己感受被污蔑的委屈。陈源对此颇为无奈地说,鲁迅说我和杨荫榆有亲戚朋友关系,还说我吃了她许多酒饭,实在是没有的啊,我和杨荫榆非但不是亲戚,简直是不认识,前年我在女师大代课,在开会的时候才见过五六面,我不代课之后,就再没见过了。
“籍”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系”,鲁迅有接着在另外一篇文章《我的“籍”和我的“系”》里面写道:
我是什么“系”呢?自己想想,既非“研究系”,也非“交通系”,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
“研究系”是当时一些政治投机人物,“交通系”是拥护袁世凯独裁的政客集团。“研究系”的成员过去是保皇党人,现在成为了北洋军阀的谋士帮凶,鲁迅曾指出,那么,想必北伐成功的话这群人肯定也要转过来拉拢国民党,点出了“研究系”的趋炎附势、投机善变。
而“现代评论派”的一些主要成员,跟这个“研究系”还真就关系密切,那么身处“现代评论派”的陈源,难道就和他们脱的了干系?陈源本想说鲁迅搞派系,结果自己却被人指出和“研究系”有难以挣脱的瓜葛,不仅没有占到便宜,还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二、鲁迅的“剽窃案”
1925年底至1926年初,北京发生了凌叔华女士的“剽窃”事件。第一件事是凌叔华剽窃图画,《晨报副刊》自1925年10月1日起由徐志摩主编,报头用了一副西洋女人黑白画像,即无署名,主编也没有声明画的来源,只是在同日刊载的凌叔华所做小说后面顺便提了一句“副刊篇首广告的图案也是凌女士的”。
10月8日这幅画被陈学昭指出剽窃英国画家比亚兹莱。第二件事是《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发表了凌叔华的小说《花之寺》,一周后《京报副刊》上有人暗指这首《花之寺》是抄袭柴霍甫的《在消夏别墅》,刘半农等也发文揭发凌叔华的抄袭行为。
当时,陈源正与凌叔华热恋。他既没有批评抄袭,也没有保持沉默,而是疑心这两篇文章都是鲁迅所作故意为难他们的。
于是陈源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五十期发表《剽窃与抄袭》一文,先是为凌叔华开脱,他说,许多情感是人类共有的,做成诗歌也不免有许多共同之处,一定要说谁抄袭了谁才称心吗?这很明显是一种诡辩,照他这个说法,那么世界上所有的剽窃行为都可以被解释作“感情雷同”了。
不仅如此,陈源接下去说,剽窃抄袭这种罪名,只能压倒一般蠢材,却不能损伤天才作家,因为伟大的作家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受过以往大文豪们思想的熏陶。换而言之,陈源在这里偷换概念,因为写文章必定受到前人的影响,于是便把受人影响等同于抄袭,故意说普通人因剽窃而受责,天才因剽窃而伟大,他要证明,剽窃是合理的。
或许在认定了讨伐对象就是鲁迅后,陈源越写越丧失理智,他的目的已经不是弄清事实而仅仅是有力反击了。他把矛头对准鲁迅,含沙射影地说,中国的批评家“俯伏了身躯,长大了眼睛,在地面上寻找窃贼”,他们能揪出来一幅画一首诗的“剽窃”,“以致大本的剽窃,他们往往视而不见”,陈源接着写道:举个例子,算了,还是不举例子了,我怕得罪“思想界的权威”。这个“思想界”的权威,指的就是鲁迅。

在含沙射影地说鲁迅有“大本的剽窃”之后,陈源在《晨报副刊》上再一次公开污蔑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日本人盐谷温著作里的一部分,那本书叫《支那文学概论讲话》。
陈源说,鲁迅作为一个大作家拿了别人的著述作自己的蓝本,也不做声明,居然还跑去挖苦一个没他有名的作者抄袭。
鲁迅一开始对陈源的表现莫名其妙,后来终于指名道姓地说自己,他站出来回应。首先,鲁迅告诉陈源,那些揭发凌叔华的文章不是自己写的。鲁迅揶揄地写道:
“可怜教授的心目中所看见的并不是我的影,叫跳竟都白费了。”
其次,鲁迅为自己做了必要的辩解,他详细地说明,自己的《小说史略》里哪一篇那几点和哪一张图是参考了盐谷温的书,剩下的二十六篇都是自己独备的论点,许多证据还和盐谷温的意见相反。如果非要说有蓝本,那么就是大家都用了中国历史作了“蓝本”。
鲁迅还告诉陈源,盐谷温的书已经有中文译本了,陈源教授要是看过的话,大概也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
但陈源这种胡搅蛮缠让鲁迅在不知详情的社会上背负了十年的“剽窃”罪行,直到十年后鲁迅的书也有了日译,中外的读者都可以靠自己的阅读来分辨两本书时,鲁迅才说,“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
陈源的这一通伤敌八百自损一千的行为,根本不是为了证明鲁迅抄没抄袭,而是为了证明凌叔华抄得有理。鲁迅抄的,我怎么抄不得?这种心态和拥有阿Q精神的阿Q“和尚摸得,我也摸得”可谓一模一样。但不管和尚有没有摸,总归是不该摸,更何况鲁迅并没有“摸”呢?
他没有耐心搞清楚基本事实,只是单纯地用自身喜好定义:他喜欢的人,剽窃了也有许多理由为其开脱;他厌恶的人,没有剽窃也要为他喜欢的人剽窃背锅。后世常认为鲁迅多猜疑,爱骂人,不过这顶帽子给鲁迅是委屈他了,给陈源倒是正好,不大不小,颇为合适。

三、一叶障目的“阿Q”
陈源和鲁迅都是现代评论派的要员,都曾在西洋留学,热衷于西式的民主和自由,因此他们的思想也有许多相似之处。
1915年,日本威胁中国接受不平等条约“二十一条”,在极端的愤慨下,全社会弥漫着激动的情绪和狂热的宣战,胡适对此十分焦虑,他写了一封给全国留学生的信,告诫他们这种“爱国癫”十分危险,因为中国目前没有可以与日本匹敌的军事力量,这样的国力在战争中只会获得一连串的毁灭。
胡适的态度在当时算是比较理性的。在胡适看来,要利用外交来开展制约,努力推迟战争爆发的时间,救国需要强国,而强国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时间。
这样看来,陈源在“五卅运动”时期的言论,也可以从胡适的观点里看出一些来。“五卅运动”始于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镇压工人罢工,5月15日日本资方枪杀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后,引发上海学生抗议宣传,被捕100余人,数万群众集中巡捕房要求释放学生,又被英巡捕射杀数十人。
事发后陈源写了《五卅惨案》表达反帝爱国思想,怒斥执政府的官员和警察。但是,在发表了带有爱国热情的文章的同时,他也发表了反对武力抵抗列强的“闲话”。他认为学生将生死置之度外,与段祺瑞政府的军警一决死战是大不值得的,他主张“据理力争”,尽管打不过人家,但要理直气壮地同人家评一评理,“不能恐怕他再打你一顿便缩缩颈跑了”。
另外,他又再次重申不应参战的观点,因为“作战是不会赢得”。这种观点似乎很像《阿Q正传》里的阿Q擅长用的“精神胜利法”,当一直被他瞧不起的小D谋了他的饭碗时,阿Q很气愤,将手一扬,唱道:“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不过在学生和政府对峙这件事上鲁迅和陈源的看法差不多,他也是反对学生们与虎谋皮的。但是在反对学生与军警冲突的问题,鲁迅的认识要深得多。“三一八”请愿那天,鲁迅故意把许广平留在自己家里抄东西,就反映了他对这件事的态度。

在请愿那天,“三一八惨案”发生了。段祺瑞卫队在执政府门前屠杀,死47人,伤199人。负陈源写过一些斥责封建军阀屠杀无辜学生的文章,并悼念死难的学生。但是,在谴责军阀的同时,他也胡说惨案要由群众领袖负责,污蔑杨德群烈士的死,是受女师大教员的驱使造成的。
不过,他并非为了造谣生事而胡说,是出于认为这场请愿活动的发起者、煽动者,鼓动了别人去死,自己却逃之夭夭,应该受到谴责的缘故。
鲁迅认为陈源的言论“比刀枪更可以惊心动魄”,他谴责道,陈源指责群众领袖就相当于承认执政府开枪是合理的,这样执政府就是一个“死地”,群众领袖带领着死者自投罗网。
这其实是一个先后问题,煽动者的确该被谴责,但排在第一的,是执政府不该随意射杀人民,放着最大的罪行不去谴责,反而揪着被害者群体不放,就相当于忽视甚至承认这种虐杀学生的举止了。
鲁迅从“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就一直首要声讨刽子手。在这样的时候,陈源仍不忘他的“公允”,只是这种“公允”,在特定的时期,实在算不上公允。
但陈源的“公允”并非一直都存在,从鲁迅“剽窃”事件可以看出,一旦伤及到有关他本人,他可就一点也不“公允”了。
当时在北大英语系读书的学生董秋芳写了一篇杂文斥骂陈源,陈源恼羞成怒,便滥用他北大英语系主任的职权,不给董秋芳发英文练习本,使他没有翻译成绩,不能毕业。
董秋芳在北河沿北大三院门口张贴申诉启事,并向鲁迅声援。鲁迅不但鼓励他的翻译整理出版,还亲自推荐到书店印行,这本书就是《争自由的波浪》。鲁迅的支持不是无足轻重的,董秋芳后来成为一名著名的翻译家。
陈源1946年任国民党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任常驻代表,1964年中法建交,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后台湾当局“大使”降旗返回台湾,而陈源奉命以中国代表名义驻馆看守。
此时陈源和陈源代表的“政府”已经不受认可,但他偏是顶着冬日严寒和断水断粮,像一个抱着破扫把不放的葛朗台,顽强独自守着,最终被法国军警强行抬出,拼命挣扎,以致血压升高当场昏厥,从此后他便宣布“引咎辞职”,常住伦敦养病。
标签: